中國學者吳思訪談錄(2):從潛規則到元規則

圖像來源,xinhua
吳思是中國著名學者及媒體人,曾經擔任《炎黃春秋》雜誌總編輯暨法人代表。此前也曾經在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任職。他長期從事中國政治史研究,首創「潛規則」概念,併發展出「血酬定律」和「元規則」論說,並主張中國共產黨應啟動、主導政治體制改革,並主動轉型為憲政制度下的社會民主黨。吳思的作品包括《中國頭號農民:陳永貴浮沉錄》、《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及《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等書。日前,吳思接受了台灣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員陳宜中博士的專訪,而BBC中文網獲得授權連載發表有關專訪內容。
陳宜中(以下簡稱:「陳」)::所以《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那本書(2001年初版),是六四之後您重新讀史的成果?
吳思(以下簡稱「吳」)::六四之後我亂了幾年。先考託福,申請出國留學。然後寫《陳永貴》,然後下海辦《橋》雜誌,後來又寫小說。寫小說寫不好,才轉向寫歷史。寫歷史對我是比較容易的事。1996年開始,先是在《上海文學》上登讀史隨筆。當時我的明史筆記已有七、八十萬字了,我就陸續把它寫出來。
首創"潛規則"
陳:您首創"潛規則"這個概念和名詞,如今它已經是能見度很高的常用詞了。您一開始是出於哪些觀察和體會,才發明出這個詞的?
吳:幹記者幹久了很容易就發現,中國社會並不是按照明文的法律規定、文件規定運作的。《潛規則》所舉的一個例子,關於化肥是怎麼分配的,就直接來自我的記者經歷。1982-83年間,照正式的規定,農民向政府賣交平價糧,不管是小麥或者棉花,收購價都遠遠低於市場價;而政府向農民出售平價的化肥,價格也應該遠遠低於市場價。以低價糧交換低價化肥,這是明文規定。
但是事實上,雖然農民向政府賣了平價糧,他們卻買不到低價的化肥。這種化肥叫做「掛勾肥」,跟低糧價是掛勾的,但是農民都說買不到。我當時從《農民日報》群眾工作部的讀者來信裏,看到一封來信說,開封地區的化肥幾乎都批出去了,批給自己的關係戶,給自己的親戚朋友。於是,我們就順著這條線索,組成了一個三人調查小組,從北京的供銷總社農資局(化肥就從他們那兒下去的)追到河南省、到開封地區,然後到縣裏、鄉里、村裏。我們發現,每一個層級都會把一批"掛勾肥「批給自己的熟人親戚朋友領導。
那麼,誰能批這個條子呢?在中國,條子管用不管用,全都有一套大家不明說的規矩,那肯定官最大的可以多批,官小點可能就不能批。一旦追問辦事人化肥哪去了,他說「條子都在這兒了」,撇清自己,並不替批條子的人隱瞞。到了最後,到農村去問村裏的農民,買到了掛勾肥嗎?都說沒買到。問他見過嗎?他說見過,隊長一袋、會計一袋。
你看,掛勾肥的實際分配體制,跟文件規定的差別巨大。只有在小部分程度上,是按正式文件的規定運作。絕大部分掛勾肥的分配,都是由不明說的規矩所支配、主導的,這讓我印象深刻。
從那時起,我開始意識到中國社會的運行有一套不明說的規則。起初我想用「內部章程」去表達它,我猜測這種現象不僅在化肥領域存在,在很多其他領域也會存在。甚至於,在中國歷史上也會有很多這類事。但這只是我的一個感覺而已,當時並沒有往下深究。直到1990年代我細讀明史,才有了進一步體會。
陳:就在您寫《潛規則》的那段時期,農村裏胡亂攤派的現象很嚴重,幹群關係很緊張。那時還沒有免除農業稅,到處都是官欺民、亂攤派。這是否也是《潛規則》成書的重要背景之一?
吳:當然。1990年代後期,我幾乎每年都到農村去調查。我有一個朋友在人民大學農村發展學院當教授,最近去世了,他當時有一個福特基金會的調查項目,追蹤三百戶農民,分佈在安徽的兩個縣和四川的兩個縣。我就跟著他們去調查,另外還有農業部政策研究部門的幾個調查項目。我在調查中看到了許多史書上提到的現象。
按政府正式規定,中共中央三令五申,農民每年繳的各種稅費,合起來不能超過總收入的5%。但是實際上,我們一戶一戶問,不管是在安徽還是在四川,農民被逼著繳納的費用大概在20%到25%之間,也就是正式文件規定的四到五倍。基層幹部總有辦法把這些錢拿到手,搜刮過來。一旦刮到了20%到25%的程度,種地基本就沒有任何利潤了,就白替人幹了,就把種地的成本都擊穿了。農民被迫把外出打工賺來的錢墊進去,去繳這些苛捐雜稅。
你要是讀明史,就會看到一些描述,大片的農田荒廢,農民乾脆不種了,因為苛捐雜稅太重,種了這個地還不夠繳錢的。不種要受罰,那乾脆就跑了,地也就荒了。我在安徽一個縣裏,看到大片的田里長著草,農民不種了、跑了。
史書上寫的那些事,全都在我眼前復活了。按照中國歷代從漢以後的官方說法,三十稅一,農民只繳百分之三點三的稅,這點稅能把農民逼跑嗎?這看起來是不可思議的事,百分之三點三的稅怎麼能逼走農民?可是,百分之五的稅顯然可以把農民逼跑,而且就在我眼前發生。就這樣,我對歷史和現實的理解一下子打通了。
「潛規則」的運作
陳:"潛規則」這個詞,現在流通很廣,其中不少語意似已超過了您原先的設定。以我觀察,至少在一開始,您寫《潛規則》主要是針對中國的官民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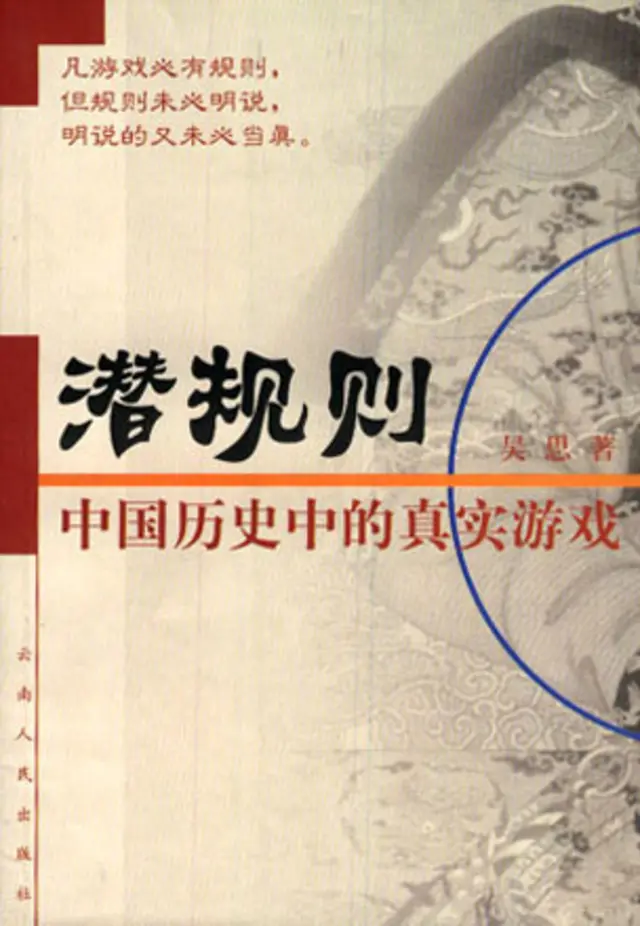
圖像來源,BBC World Service
吳:首先是官和民的關係,但也包括官和官的關係,以及官和上級之間的關係。官和民的關係,如果你看大明律或唐律,都有一套以官為主體的規定。吏、戶、禮、兵、刑、工,都說得很清楚,但實際的運作卻不是那麼回事。剛剛已經說了,管稅的戶部,就不是按明文規定去辦事的。刑部,例如法官賣自己的權力替人減刑,這種事也很普遍。像這樣的官民關係,古書和史籍都有很完整的紀錄,也有相應的概念提出。例如各種羨耗、鬻獄等等,明清把這些統稱為陋規,而「潛規則」其實就是陋規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只是沒做道德評判。「陋規」是加上了道德評判的,「潛規則」這個詞就比較中性。
第二個是官和官之間的關係,這整套陋規也是非常完整的,包括怎麼送禮等等。我書中引了高陽先生舉的例子,那是講官員派人送畫到北京的琉璃廠估價,細節在這裏就不多說。當然,送禮現在是更加爐火純青了,包括大陸整個的藝術品市場,跟台面下的送禮很有關係。此外還增加了各種金融手段。
陳:包括「跑部錢進」,辦法多的不得了。
吳:「跑部錢進」不是新鮮事,「部費」其實是清朝的概念,指的是向吏、戶、禮、兵、刑、工各部送的陋規。只是現在不叫部費,叫跑部錢進。這類潛規則還包括,如果你從社科基金拿到比較大的課題費,你得給社科基金的主管官員多少回扣。這些規矩誰都不明說,但是各行業的人都知道。如果你不照辦,就會受到各種刁難和處罰。
另外,還有官和上級之間、皇帝之間的一套潛規則。
陳:除了錢權交易的雙方,還有「被潛」的第三方?
吳:順著我的邏輯進一步講,潛規則的運作應該是一種三方關係。除了通過潛規則交易的雙方,應該還有一個第三方,譬如說公共道德或者法令代表,或者是上級(但是這裏所說的上級,必須是正式制度法規的代表)。如果我是個官員,我行使的權力是我所代理的公權力,這個公權力不是我的。當我把這個權力出售給你的時候,不管是減刑還是免稅,或提供給你其他好處,肯定是不合法的,或者不合乎公共道德。正因為說不過去,才必須瞞著,才一定得潛。
「潛規則」與社會環境
陳:有些問題我不是想得很清楚,想請您再做些說明。比方說,剛剛提到亂攤派的例子。朱鎔基搞了分稅制以後,地方政府的財源不夠,也沒法把地方官員裁撤掉,於是地方官就去盤剝農民。但如果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有所調整,也許就不至於剝削到25%?從這個角度,潛規則運作的「烈度」,跟宏觀的政治社會基本面是有關的?
吳:肯定和宏觀的政治社會基本面有關,但基本面也需要分開來說。從結果看,2004年取消農業稅之後,各種苛捐雜稅失去了乘車收費的依據,合法傷害權沒了,盤剝農民的難度大幅度提高,各種潛規則基本消失。在這個意義上,取消農業稅就是最大的基本面。相比之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關係是第二位的。
在取消農業稅之前,各個鄉鎮存在大量冗員,四五十人的編製,通常有二百人上班,他們以前吃潛規則的飯,現在沒飯吃了,被迫另謀生路。2009年我去安徽農村調查,看到一個鄉政府的辦公室裏掛著工作人員的分工名單,名單上只有五十來人。我問他們原來有多少?回答說將近二百人。這些人去哪裏了?大概有三條出路,這裏不細說。反正這裏沒有飯吃,這些人才會走。這裏有飯吃,吃得好,人就會增加,然後超編,越超越多,搜刮隨之愈來愈重。最後,征收上來的各種稅費,甚至不夠支付這些冗員的工資。這樣的稅費基本成了人頭費,與地方政府承擔的公共事務,其實已經沒有多大關係了。
陳:您曾用「合法傷害權」去詮釋潛規則。但您也提及「被潛」的第三方,譬如法令代表或公共道德。那麼,以私害公的「傷害權」何以是「合法」的呢?
吳:所謂合法,主要指加害者的權力有合法的來頭。官員行使權力一般被認為是合法的。進一步說,行使權力的過程是否合法,也有一個從簡單到複雜的模糊地段。
先說最簡單的,刑法規定某罪可判五到十年,那麼,判五六年也合法,十年八年也合法,這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這個自由就可以做交易。
再說複雜點的,例如各種農業稅費,雖然總額限制在5%之內,但是具體哪一筆費用在這5%之內,農民搞不清楚,官員征收到25%,似乎每一筆都是合法的,你拒繳任何一筆都是抗法。
更複雜一點,地方政府在自己的權限邊緣收了一筆費用,例如徵糧時工作人員的一點加班費或誤餐補助,民眾想少排隊也不反對,這是否合法呢?
最後才是以權謀私,敲詐勒索。這麼做並不合法,但成本很低,風險很小,我稱之為「低成本傷害能力」。合法傷害權呈現為從白到黑的一個灰度系列。
「潛規則」與「交易成本」
陳:您表示潛規則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這個提法跟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有關嗎?「交易成本」概念的始祖是科斯,他起初是在公司理論的脈絡下談的,他說通過市場機制進行交易的成本,有時要高於公司把這些成本給內部化。後來,很多人就把「交易成本」概念擴大化了。在大陸,我不確定「交易成本」最早是不是張五常推廣的?按張五常那種說法,所謂的腐敗、錢權交易、行賄、走後門等等,基本都很OK,因為這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甚至是一種必要的潤滑劑。
我多少擔心「降低交易成本」之說會有負作用。比如說,第三方(正式法規與公共道德)被潛,這本身不就是一種社會成本?張三行賄官員李四,買到了污染環境卻不受罰的好處,李四也從受賄中得利,但這種潛規則的運作到底降低了誰的交易成本?哪一種交易的成本?在這類案例中,「降低交易成本」之說可能會讓人覺得:反正中國社會就這個樣,為了降低我的交易成本(如靠污染髮財的成本),我應該明智地按潛規則來辦事。曾經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嗎?
吳:沒人這麼問過我。在追問誰的交易成本方面,你是第一個。
「交易成本」這個概念,最初我是從天則所(天則經濟研究所)那裏接觸到的,他們走的就是科斯的路子。張五常寫過「交易成本」的詞條解釋,他的確是把它泛化了,好像只要有了人與人的關係,例如魯賓遜和星期五,就有了這種成本。狹義地說,交易可以專指經濟交易。一旦擴大化,你甚至可以說戰爭也是一種交易,因為兩個人之間可能出現戰爭、搶劫。但實際上,我們都知道搶劫不是交易,威脅你要錢要命也不是交易。「交易成本」一旦泛化到了經濟領域之外,進入政治領域,進入戰爭和軍事領域,就已經不叫交易了。
然而,我們又沒有其他概念去表達人際交往的成本。如果不叫交易成本,例如以「交往成本」去代替交易成本,也得大家都認了這個詞才行。如果不肯泛用交易成本的概念,我會選擇使用交往成本。可我認為名詞不是最重要,實質表達的意思應該更重要。我對潛規則的基本定義,包括了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現在如果改用交往成本,意思還是一樣的。
潛規則之所以成為規則,是因為雙方都形成了固定的預期:我給你這個錢你會辦這個事,我如果不給你這個錢,你又會如何懲罰我,等等。如果雙方沒有這樣的預期,你想讓我多繳我就是不幹,然後你想盡辦法收拾我,那就對抗了起來,交易成本就很高。
其實,說腐敗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說它有助於經濟體制改革,能讓這個社會的改革加速,我在事實判斷上是接受的。從道德判斷上說它不對,是錯誤的,也說得過去。但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比較複雜,很難一概而論。如果說人民公社是憲法規定的,如果說違憲的東西就必須禁止,那「大包幹」(改革開放初期的包產到戶實驗)是不能生成的。
當時安徽鳳陽縣小崗村農民之間的協議是,我們搞大包幹,但是不要讓上面知道。如果我們之中有人因此被抓起來了,關進了監獄,大家要出錢把他的小孩養到18歲。這就是一個潛規則,瞞著領導,瞞著上面,但它本身是出於對惡法的規避。
如果小崗村所在的鳳陽縣的縣委書記,不肯睜隻眼閉隻眼,而是說你們違法違憲了,給我退回去,這完全是正當的。假設小崗村向他行賄,說請你假裝看不見,我們分你10%。而如果他真這麼做了,他就是腐敗分子,但他的腐敗卻讓大包幹活了下來,使農民受益。那你說,這種腐敗對於大包幹的存在和發展,不是起到了正面作用嗎?
當然,歷史事實不是這樣。當時的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同情農民,暗自支持大包幹。地委書記王鬱昭和省委書記萬里,也站在小崗農民一邊。我們看到道德、權力站在了潛規則一邊,法律和憲法站在對面。但其他組合也是可能的。
在事實層面上,當年英國貴族向資產階級讓步,是因為他們自己都開始做生意了。中國大陸的官員為什麼能向市場經濟讓步?部分原因是,這也為他們帶來了好處,而這好處可能是權錢交易帶來的,但市場經濟也因此減少了前進的阻力。你當然可以從道德意義去指責他們,可是道德跟歷史後果往往是兩回事,在中國尤其如此。
陳:是否可以說,「潛規則」的實際社會效果很難一概而論?有些錢權交易起到了好的作用,也有些錢權交易讓農民買不到低價化肥,等等。
吳:對。潛規則的實際社會效果,取決於上邊那個正式法規的性質。如果正式法規是惡法,或者錯了,過時了,有瑕疵等等,相應的潛規則就有不同程度的正面作用。如果潛規則試圖規避的正式法規很好,很公道,相應的潛規則就有負面作用。道德是另一個評價維度,有可能站在法規方面,也可能站在潛規則方面,需要具體討論。
「血酬定律」與「元規則」
陳:您從對潛規則的分析,進一步發展出「血酬定律」和「元規則」概念。「血酬」是指流血、暴力所能得到的報酬。「元規則」是指暴力最強者說了算的meta-rule。您提出「血酬」的主要思路是什麼?「元規則」有歷史或社會本體論的意味,突出強調暴力是主導一切表面規則的終極規則。
吳:血酬的主要思路,就是參照經濟學分析生產要素的思路,分析暴力破壞要素,或者說,把暴力要素引入經濟分析。在中國,我們到處都看到權力的作用,合法傷害權的作用,或暴力的作用。我從《潛規則》轉向《血酬定律》,是因為我把官和民、官和官、官和皇帝的關係都寫完之後,發現背後都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我認為,潛規則所涉及的交易成本,主要來自破壞要素,或者叫暴力要素。於是,我想進一步對暴力要素的投入和產出,給出一套比較完整的說法。
比如說,一個搶劫者玩命,投入了流血掉腦袋的風險,他的投入跟回報的關係是什麼?如何描述這種回報?這一定得有一個概念,我找不到現成的,所以我被迫造一個新詞叫「血酬」。暴力要素的投入和產出之間的關係,我叫做「血酬定律」。順著血酬定律的思路,我覺得我的眼界比過去更開闊,分析中國也變得更順暢了。
血酬就是暴力掠奪的收益。如果暴力掠奪奪到的是天下,打下了天下坐了江山,就不必刀刀見血地去搶了。這時可以立一個制度,讓人來繳保護費或皇糧。譬如收了一百億的稅,用之於民五十億,總得幹些維護社會治安的事,然後再用十億維持政府的運作,剩下的那四十億就揣在自己兜裏了,去包二奶包三奶,去養後宮去修皇陵等等。總稅收一百億減去用之於民和維持政府運作的六十億,剩下的四十億就叫「法酬」。法酬等於全部稅收減去公共開支,由於我找不到已有的表達方式,就順著血酬的思路把它稱做「法酬」。法酬是血酬的升級版,是在血酬的基礎上,有了某種合法外型的一套收入,但仍然是暴力掠奪的收益。

圖像來源,BBC World Service
血酬定律跟元規則有什麼關係呢?血酬定律說的是暴力的投入和產出,簡單來說就是三條。
第一,血酬就是暴力掠奪的收益。
第二,血酬定律是指當暴力掠奪的收益大於成本時,暴力掠奪就會發生。換句話說,暴力掠奪行為與收益正相關,與成本負相關。這是一個事實判斷。
第三,暴力掠奪不創造財富,於是就牽涉到暴力掠奪集團跟生產集團的關係問題。「元規則」是決定規則的規則,在歷史事實上,這個元規則就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當然,暴力最強者也不能一意孤行,他要考慮到生產集團會不會偷懶,民眾會不會反抗、逃亡,然後尋找一個最佳的掠奪率,不管是稅率還是對自由的限制。元規則的主導者是暴力集團,是暴力最強者;他們計算成本收益的算法,是用血酬定律來描述的。
陳:您用「官家主義」這個詞來界定秦漢至今的中國社會,也是通過研究血酬所得出的?
吳:有很大關係。從血酬定律和元規則的角度看,中國歷史呈現為一個又一個暴力集團的崛起。他們打天下,坐江山,建立大一統帝國,立法定規,吃法酬,然後被另一個暴力集團推翻,如此循環不已。如何稱呼這種社會?大陸一直把秦漢以來的社會稱為封建主義社會,但我們知道,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封建制度到他那裏就被廢了。這個變化,從暴力資源分佈的角度可以看得很清楚。
秦漢之前,暴力資源是分散的,小國林立,呈現出中小貴族架著大王的結構,統治金字塔上的每塊岩石都是擁有暴力的政治實體。秦把郡縣級封建貴族換成了代理人,代理人不能世襲,沒有私人武裝,岩石金字塔變成了金字塔形的鐵架子。暴力資源集中到最高統治者手裏,各級文武官員都是皇帝的代理人。隋唐之後,更要通過科舉考試選拔代理人。為了和封建主義區別,我把這種社會稱為官家主義社會。
用經濟組織比喻,封建主義好比商會,眾多老闆推舉一個有威望的老闆當會長。官家主義好比上市公司,老大率領眾弟兄艱苦創業,打下江山了,好比公司上市,論功行賞,封公封侯,老大當皇帝當董事長,然後杯酒釋兵權,讓其他創業者退居二線當股東,另外聘請一些MBA當經理。這時候封建是虛封,有名無權,官僚治理才是實的。所以,官家主義比封建主義更凖確。
當然也有其他現成的稱呼,例如東方專制主義,皇權專制主義。但是,無論是東方,還是皇權,都不如官家凖確。官家這個詞有三個釋義,一指皇帝、二指官府衙門、三指官員個人,中國古代誰能「主義」呢?如果把主義的「主」理解為當家作主,把主義的「義」理解為規則的話,在中國古代當家做主立法定規的正是這三個主體。皇帝立法就是王法,衙門立法就是部門法規或地方法規,官員個人立法就是潛規則。
這三者之間經常勾心斗角爭奪地盤,但作為一個整體,官家才是主義的力量。皇權專制主義的概念無法顯示官員個人所主導的潛規則的存在,也看不出地方或部門法規架空皇權的政治格局,例如藩鎮割據,或毛澤東所說的「條條專政」——中央各部門自行其是,不把皇帝的旨意當回事。我們知道,在中國歷史上,潛規則和各種割據都是導致王朝解體的重要力量,官家主義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分析這些力量,而皇權專制主義的概念卻遮蔽了皇權之外的力量。東方專制主義的概念就更模糊,連中國和日本這兩個東方國家的重大差別都被遮蔽了。
陳:您曾經表示血酬史觀最適用於暴力主導的社會,但您堅持「元規則」也適用於當代的憲政民主社會。我在網上看到一篇胡平對您的評論。他從憲政民主的視野,質疑您太過強調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極大化,也太過單面向地強調暴力因素。不知您有何回應?
「暴力最強者說了算」
吳:我認為「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條元規則,跟憲政民主並沒有衝突。在憲政民主國家,例如美國,誰是暴力最強者?總統是三軍總司令,而總統是選民選出來的,因此,選民或公民就是暴力最強者。立法機構的議員也是選民選出來的,他們代表選民立法定規。總之,公民作為暴力最強者決定各種法規和政策及其實施。元規則,決定規則的規則,暴力最強者說了算,對當代美國顯然很適用。
我確實接受人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我認為,只要把利益的定義放寬一點,不把利益全等於金錢,這就是一個事實描述。每個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時候都明白,你其實不僅僅追求錢,你的人性非常複雜,你會在乎你的安全,會在意內心的安寧,也會有同情心和正義感。按孟子的說法,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些人性收益也包含在我所謂的"利益」裏面。
追求利益最大化,也可以和民主憲政兼容。從群體角度看,利益最大化有三種:民族整體利益的最大化;統治集團利益的最大化;還有民眾利益的最大化。從中國歷史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官家主義體制從秦漢一直到清,如果只算大一統帝國(不算五代十國和魏晉南北朝),平均壽命是一百七十一年,時候到了就死。如果把五代十國和魏晉南北朝也算進去,平均壽命是六十六年。死因有三條:40%死於民變,40%死於官變,還有20%死於外族入侵。
官家主義體系控制不了這些因素,到了時候就死。一旦死了就一塌糊塗,民苦官也苦,統治集團也好不了。為了統治者和民眾的雙方利益的最大化,為了民族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憲政民主制度是合算的。
我對暴力要素的強調,是就歷史事實而言。在人類歷史上,暴力行為比生產行為更早出現,要早的多。為什麼人會生產?如果那些猴子猩猩能以很低的成本去搶劫,收益很高、成本很低,為什麼不繼續搶?在這個意義上,出現生產行為的一個隱含的前提是:暴力掠奪的成本太高。生產行為的出現是因為暴力掠奪不合算,這個簡單的歷史事實證明,暴力收益或是血酬的計算具有根本性。
陳:您提到「民族整體利益」,不知您怎麼看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
吳:由於中國政府不斷強調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有了一種公開表達、暢行無阻的合法性,所以顯得聲勢比較大。但是在知識分子當中,很多人是對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保持警惕的。
談民族主義可以,但應該對民族最大利益有個清晰的表述。如果你的民族主義只說愛國愛國愛國,卻不談這個國要變成什麼樣才會可愛的話,那你沒有解決根本問題。
自由主義者說,這個國應該尊重每一位公民的權利,不能是一個貪官污吏遍地的國家;應該實行民主憲政,而不能是一個專制的國家;這樣的民族才是一個值得尊敬的民族,一個可愛的民族,才是一個可愛的國家。我是支持這個觀點的,所以我認為民族主義不是一個終極的主義。我對於那種民族主義的熱鬧吧,始終有所警惕。
(責編:李文)
網友如要發表評論,請使用下表:
讀者反饋
吳老師說的很對。每句都對。
孫立林,
我與吳思是同時代的人,同屆大學生,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經歷,儘管我理解吳思對極左的踵情和執著。
吳思極左的經歷,是我們這代人非常熟悉卻完全不親切的記憶,沉重、痛苦又抹不去。
我出自於與之完全相反的家庭環境和背景,或許這是我有著更為深入的思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吳思的大學專業以及畢業分配到中央直屬機關工作,極左經歷由深陷其中到迷惘徬徨、由甜變苦的另一原因。正是因為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大學專業、極左的經歷和畢業分配的幸運,加上自己的執著努力,使其成為知名的學者,就像當年學俄語專業的人更容易受到重用和更容易成為翻譯家一樣。
人,不一定非得有極左的經歷才能悟出極左的危害,儘管比較有說服力。人生的真正價值,並不完全是為了對後人做經歷上的啟迪,雖然看上去很崇高和動人,卻很難讓人對其本來就該有的良好判斷產生敬意。遺憾的是,走過彎路的人比沒有失誤的人更給力,更有學術價值。
我是同年學習英文專業的,是抱著對社會,對紅色制度,尤其對毛澤東變著花樣無窮無盡的政治運動和不變的愚民政策的厭惡,對從中文資料掌握知識,觀察世界的不信任決定自學英語的。我慶幸沒有走過彎路的極左經歷,更慶幸自己的觀察和判斷,在漫漫寒冬的黑夜裏,耐心等來暖春的到來。
二十五年前的初春,仍寒意襲人。
可算盼到了,儘管來的太晚太遲!
韓尚笑, Sydney Austral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