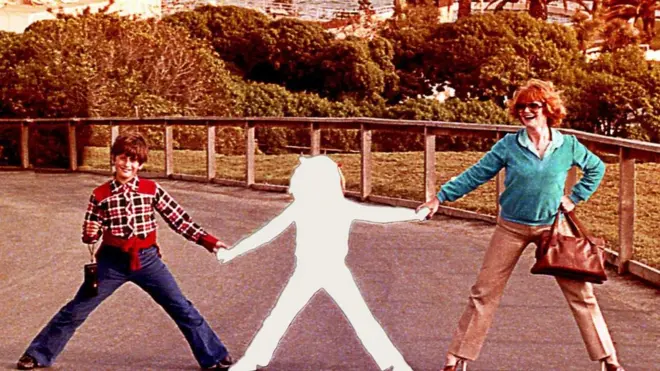台湾长女作家写“长女病”:“蜡烛型人格”的家庭和职场辛酸

图像来源,PROVIDED
- Author, 吕嘉鸿
- Role, BBC中文
你是长女吗?
或许你听过“长兄如父,长姐如母”的古谚,这句话道尽东亚汉人传统家庭的排序逻辑:长子传承家业,长女辅佐家务。
但是,根据台湾作家张慧慈的调查,东亚社会许多长女们,不仅辅佐家务,还时常牺牲自我发展或身家财产给家庭。
她以自己的经验及研究,写下《长女病:我们不是天生爱扛责任,台湾跨世代女儿的故事》一书。该书2025年面世,在台湾掀起广泛讨论,一度登上书市畅销榜,并即将翻译成韩文出版。
书中探索的“长女病”其实不是生理疾病,而是心理与社会结构的产物。BBC中文访问了张慧慈及年轻的台湾女性及相关学者,探讨这个在台湾舆论场热议的话题。
姑姑的遗言:“以后你会懂我说什么”
在张慧慈的记忆中,姑姑的离世是难以磨灭的记忆。姑姑病殁前说的最后几句话,触发张慧慈多年后探究长女议题的灵感,最终成书。
张慧慈忆及,那是一个寻常的台北下午,因为一生劳碌、40岁便罹患胰脏癌症末期的姑姑从台湾南部北上探望家人。
她说,小时候很不理解,为何自己和姑姑同为长女,她却明显更疼爱二妹。当天,她终于从姑姑的口中得到解答。“因为妹妹她活得很自由自在,这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我做不到。”
姑姑向张慧慈说,我好羡慕她。“慧慈,在这个家族里面,做大姐的就是没有办法做什么,可是这是不公平的。”
她忆及,姑姑叮咛说,“以后不要活得像我一样,要去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出去走走,然后要好好地读书然后去赚钱,走出去,不要被这个家庭影响。你现在可能不知道姑姑在讲什么,可是长大后一定会知道。”
这句话对张慧慈来说不仅是最后的叮咛,似乎还有世代相传的心意传承。
张慧慈说,姑姑一生劳碌,从少女时代起便肩负照顾家族与外甥的重担,为了孝养父母与论及婚嫁的外地男友分手。之后甚至过继妹妹无力抚养的孩子为干儿子——不仅承担女儿该有的角色,还为家族延续做出牺牲,却因为未婚身份被家族亲友鄙夷,即便过世了“许多亲友对她都没有什么好话”。
她后来回想,这不仅是姑姑的命运,更是无数台湾“长姊如母”的缩影——她们被教导要“撑起家”,却鲜少享有回报。
姑姑过世后,张慧慈遵从遗言,埋首书堆,试图以学业翻转命运,她在清华及台湾大学拿下学士硕士,在成年后逐渐发现,自己的这份“长女责任感”已如藤蔓般缠绕着自己生活却难以挣脱——即便遇到严重的职场霸凌。
在意识到自己这个“症候”时,她求助专业心理谘商,又发现周遭际遇相似的女性朋友们,也多数是长女!这让社会学背景的她开启了对“长女病”的研究。

图像来源,PROVIDED
长女病到底是什么?
“长女病”究竟是什么病?还是做长女就会生病?
对此,张慧慈直接向BBC说, 其实没有长女病这个“病徵”,她自己定义长女病好似是一个社会特质 (social character/trait)。譬如如果妳是一个可能要负担家计,或者是说从头到大背负过多的家庭责任的话,那你就很容易在行为上会出现过度承担,甚至是牺牲自我,十分在意父母的想法,委屈自己去做所有的事情。
那为什么是社会特质?
对此,张慧慈称长女病会出现,是因为社会需要有人来承担很多责任,然后这些人最好就是都不要有任何的怨言或反抗,加上父权意识形态与社会的协力,创造了“长女”这一批人。
“然后告诉你作为大姐该怎么做,要长姐如母。作为大姐就好像什么事情我就接上,特别是华人社会的女性来讲,好像就一切都那么理所当然的感觉。”她说。
此外,有一些分析也强调,虽然许多人提及长女病似乎是上世纪出生的女性,但对年轻的女性来说,上一代的家庭角色,还是复制到年轻的台湾女性身上。

图像来源,Emmanuel Lafont
就读研究所并从事自由业多年的台湾女性Yufeng(化名),也在网路抒发自己身为长女的感叹,认为张慧慈出书终于为许多长女发声。
90后的Yufeng向BBC解释,她是从小被父母长辈叮咛“姊姊要让弟弟”时开始意识到长女的挣扎,譬如爸爸会向她说:“这是你的弟弟,你以后要负责照顾他”。
Yufeng又指出,随着年岁渐长,一些涉及到家庭责任的事务,总是姊姊承担。“例如:妈妈的事业需要姊姊投资、爸爸想买房期望姊姊能负担贷款,小事就是过年回家,姊姊总是被招唤的那个,而弟弟爱不爱回家都无所谓,也不会被强求,爸妈询问也是透过姊姊再问弟弟。”
“高中时期、大学时期,爸爸来跟我借钱,家里的人总会说,怎样都是自己的爸爸,期望姊姊能承担一切,不过我内心是想跟那些亲戚们说,那也是你哥、也是你儿子。我意识到这点后,因此决定不想因为家里而牺牲什么实际的东西。”
Yufeng说,她常被呼唤回去照顾生病的奶奶、帮妈妈处理电视坏掉、手机不会用的问题等,但弟弟不会被呼唤。
“我认为我很早觉醒身为长女会被压迫,以及对于压迫会反抗。”Yufeng表示。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长女的“蜡烛型人格”
心理学将这种人格称为“蜡烛型人格”——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另一心理学学派提出相关的“手足排序理论”指出,这种性格不限于生理性别:主要指那个“没人指名,却总是自己走进责任里”的人。
有一位读者在网上分享:“小时候,爸妈忙,我就煮饭带弟妹;长大后,职场上也总是加班到最后。”有研究称这种模式,横跨蓝领与白领家庭,也横跨世代。
张慧慈说,的确在职场上,更容易嗅出谁是长女。
她根据自己的初步调查指出,若我们稍加留意,不难辨识出长女身影:她们总是默默完成任务、主动扛起不属于自己的责任,甚至容易遭受霸凌或自我PUA(自我怀疑)。
换言之,这些女性习惯“横向照顾”,从家庭延伸到办公室,成为团队的“稳定器”,却也因此忽略升迁与界线。但张慧慈坦言:“当主管时,我特别喜欢聘用长女,因为我知道给她们公平的待遇,她们会忠诚负责地回应。”
这似乎道尽长女的职场优势:高适应力、强执行力,但也暴露隐患——她们容易被剥削甚至霸凌,却鲜少发声,自我怀疑也很严重。张慧慈解释,长女常习惯自力更生:因为从小要负担弟弟或妹妹不乖带来的风险,所以在办公室通常都有“算了,我自己来比较快”的个性。
这种独立,从家庭延烧到职场,让她们宁可加班,也不愿求助他人。譬如一位白领女性向张慧慈分享:“入职第一天,老板丢来一堆杂务,我以为是考验,结果成了常态。加班到深夜,却从未争取加薪。”
另一位受访者说:“我总是帮上司写报告,换来一句‘你真可靠’,但升职机会永远轮不到我。”另一位教育工作者则说:“同事休假,我自动接手;疫情时,我一人扛全班防疫,却被指‘太爱出风头’。”
这些经历,反映长女的“蜡烛型人格”:她们有可能比较服从权威或在职场上唯命是从,原因来自自小在家庭中对父母长辈的命令需要使命必达随传随到。
在社交网路平台上,一位用户这样说:“长女病让我在职场上永远是‘好员工’,但内心空虚到崩溃”。台湾精神科医师洪敬伦也在网路上指出,在台湾文化中,“姐姐要让弟弟”或“大的要帮父母”这些观念将“照顾他人”内化为长女的身份职责。“它不只影响心理健康,也让许多人错过了探索自我、尝试错误、或单纯休息的自由。”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人。她从小照顾弟妹,学业优秀又能干,但在她心里仍有遗憾:太早成为小大人,错过了能自由做梦的童年。”洪医师说。
全球共同的“长女”现象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长女病”并非台湾独有。根据研究,在韩国的“K-长女”(K-장녀)(是韩国“Korea”的与“长女”的组合词)同样指在传统韩国家庭中,长女被期望要牺牲自己、照顾弟妹与家庭,养成过度懂事、以他人为重、忽略自身需求的人格,与华语圈的“长女病”概念对应。
近期Netflix韩国电视影集《苦尽柑来遇见你》便以此为题材,探讨三代济州岛长女的命运。有心理师分析,剧中长女的特征——早熟和隐忍——正是亚洲家庭的缩影。
据此,张慧慈向BBC透露,书出版后,不仅中国大陆读者大声附和拒绝成为“扶弟魔”,连懂中文的韩国与印度读者,也纷纷传来感同身受的回响。
“扶弟魔”是中国网路流行词,指女儿无条件牺牲人生,成就弟弟:从小让玩具、到成年资助婚房,甚至挖空家财还债。一位中国大陆读者向张慧慈说,自己到英国留学,父母立即要求开始工作后,需要存钱帮弟弟买房,她提出质疑后遭致父母反驳称“因为你是姊姊。甚至没有拒绝的空间。”
另一位懂中文的韩国釜山读者则向张慧慈分享,她是泪流满面把书读完,直说这是她的故事。
去年获得釜山影展最佳导演的台湾影星舒淇半自传的电影《女孩》则透过影像直指基层家庭中,长女不堪家庭肢体及性暴力的出走,代表台湾正角逐奥斯卡外语片的《左撇子女孩》里,台湾导演邹时擎也聚焦在单亲家庭中,年轻长女面对未来的迷惘与坚韧。
美国红星泰勒丝(Taylor Swift)最新发行的专辑一首新曲《Eldest Daughter》也在高唱长女的挣扎与荣光。歌词细腻描写称“长女,总是第一批被送去屠宰场的羔羊,因此我们披起狼皮,无畏无惧!”
这首歌一推出,便登上Billboard热门,有粉丝留言:“终于有人懂我的痛。”
如何卸下长女包袱?
张慧慈向BBC说,她与朋友去心理谘商时,谘商师都向她表示“你们长女”是谘商大客户。
事实上,许多心理谘商师或精神医生也陆续提及“长女”在她们的治疗间不算少数,常因“无法休息”或不断付出(不管对方是否需要)出现忧郁等健康问题而求助;譬如,台湾振芝心身医学诊所洪敬伦医师撰文指出,临床工作中常到长女或家中最体贴的女儿,而这些女性从小就在一种“被需要”的期待里长大。
“随着时间推进,这些期待逐渐内化成一种心理惯性:习惯让自己有用,习惯在混乱中维持秩序,也习惯把‘让别人安心’当成价值所在。然而,当这种惯性长期运作,‘功能’会悄悄取代‘自我’。”换言之,自我来自别人对她们的依赖。
如何协助长女们卸下重担?
对此,心理学学者、香港理工大学助理教授许沛鸿(Bryant Hui)向BBC中文说,从整体研究来看,现今的研究尚未证明出生顺序与心理健康之间有坚实或一致的关联性。
譬如,大规模研究和元分析(Meta-analysis)并未发现与抑郁或一般心理困扰等事物之间的可靠连结;此外,大多数心理学研究亦显示,即使存在某些轻微影响,其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
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性格研究员朱莉娅·罗尔博士(Dr Julia Rohrer)也曾向BBC指出,“长女病”确实提供了一个框架,让女性可以找到在类似情况下成长的其他人交流经验。她认为,以这种方式框定个人经历无妨,反思自己的经历也很有意义,“但只要你不认为这种经历是普遍的”。
许教授也向记者强调,就心理健康来说,在家庭中建立支持性的关系和健康的沟通,远比一个人的出生顺序重要得多。

图像来源,Emmanuel Lafont
台湾读者Yufeng向BBC中文表示,她认为长女照顾人“应该不是小福利”,因为“对别人来说是福利,对于自己来说很累人。但她说自己也没有不喜欢当长女,“长女幸福的点是作为第一个小孩受到许多喜爱,也因此有情感上的包袱,需要承担更多。”Yufeng笑称,这“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可能近似“能者多劳”的概念。
据此,张慧慈同意当然许多长女自小就被视为掌上明珠备受呵护,也有忍受不了很早就反抗家庭权威的长女等。但她对仍在亚洲背负长女包袱的姐妹及家庭们喊话,表示要解开长女病的枷锁,从父母态度与手足有意识的“家务分工”是重要的一步。
她以之前母亲生病,可能需要家属“捐肝”为例。当时候她又想一肩扛下,直到弟弟妹妹告诉她说,“我们也有心要一起承担”,她才意识到自己可以把责任分出去。
精神科医师洪敬伦则说,他期盼长女能尝试放下种种期待,“包括对自己的要求,留一点空间给呼吸与迟疑。当你愿意这么做,生命会慢慢松开,会重新看见那份属于自己的力量。”
张慧慈也说,长女须学会爱自己,这不是自私而是对自己的基本最尊重与爱,有健康的家庭及社会是人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