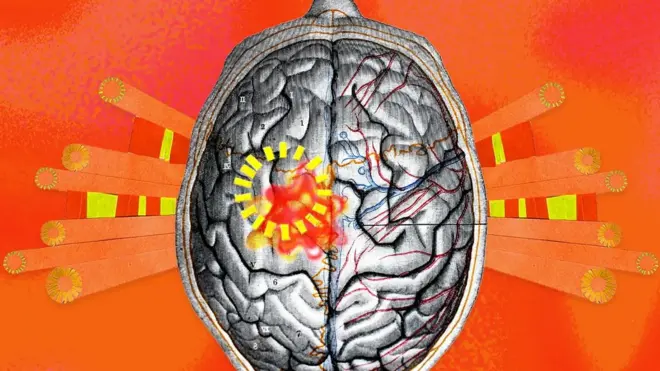關於多巴胺,我們都搞錯了些甚麼

圖像來源,Serenity Strull
- Author, 尼古拉·庫庫什金(Nikolay Kukushkin)
我們的大腦是極其有用的器官。但看來,我們與大腦的關係似乎出了點問題。
身為人類,我們常常覺得自己正與自己交戰。我們渴望得不到的東西,卻又需要我們不想要的東西。我們會沉迷於壞事,對好事失去興趣。我們反覆思索、執著、發脾氣、懊悔。彷彿總在試圖抵達某個更飽滿、更完善、更完整、更自然的人生版本,卻始終無法到達。
為甚麼我們與自己的大腦如此失調?事實上,原因很大程度與一種特殊、但常被誤解的神經傳導物質多巴胺(dopamine)有關。正是多巴胺,主導著身體驅使我們不斷尋求「更多」。
人們往往傾向認為,現代人的生活是不自然的,使我們無法實現某種原始的快樂,而我們的祖先大概都享有過。穴居人沒有薯條,所以不用擔心肥胖,也不必強迫自己去健身。他們天天在森林中散步,從容採集堅果和莓果,攝取充足纖維。他們沒有金錢、工作、婚姻、宗教或藥物,因此不存在不平等、暴力、嫉妒、等級制度或成癮。只有當我們從這個採獵天堂轉向農業與文明的誘惑時,我們的生活才變得與生物需求如此不協調。
當然,這種無憂無慮的過去其實並不真實。我們對採獵祖先的心理狀態所知甚少,但有一件事可以確定:他們與我們一樣易怒、坐立不安。我們對生活的挫折並不新鮮。事實上,這種挫折是設計的一部分——其根源遠比文明更古老,甚至比人類這個物種還要久遠。
正是這個設計讓我們永遠處於煩躁不安中,戲弄我們、刺激我們,像來自古老動物本能的聲音,在耳邊低語:你所擁有的,並不是生命的全部。
我們本來就不應該因已有的東西而感到滿足。我們本來就是要不斷尋求更多。
要理解原因,我們需要看看大腦中兩個部位——大腦皮層(cerebral cortex)與包括多巴胺在內的獎賞系統——如何驅使我們朝不同方向前進。
沒有多巴胺的大腦
大腦皮層是我們用來理解世界的萬能機器。它為我們建立現實模型,然後努力讓模型與外界一致——或反過來,使外界與模型一致。它想要的不是準確分析,而是以任何方式,最大程度地讓現實與期待保持一致。
這種追求「最大一致性」的驅動力有個明顯問題,有時被稱為「黑房間問題」。如果皮層只想要內部的一致性,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找個黑暗房間的角落:切斷所有感官輸入,如此一來便不需解釋或調整任何事。
顯然,這套機制並不完整:必然還有某種力量,推著皮層走出無經驗的黑暗房間,進入充滿新奇、驚喜、目標與成就的世界。事實上,大腦確實有另一個模組,其整個存在目的,就是策動這樣的推力。它就是獎賞系統,而多巴胺便是這個系統用來引導我們決策與動機的主要工具,一種既巧妙又近乎魔鬼般的工具。多巴胺讓我們持續往前走。

圖像來源,Serenity Strull
要理解這一點,觀察當人完全缺乏多巴胺時會發生甚麼會有所幫助。一種名為嗜睡性腦炎(encephalitis lethargica)的神祕疾病,於1915至1926年席捲全球,提供了可怕的案例。這大概是由常見喉部感染的併發症引起,而在少數患者身上,免疫系統錯誤攻擊大腦,使他們陷入嗜睡狀態——不是完全昏迷,而像是一種無反應的清醒。
有些患者偶爾會說一兩個詞;有些在球被丟向他們時會伸手接住;食物放入口中,他們會咀嚼——但從不會主動伸手去拿食物。如今我們知道,這種狀況特別影響了大腦的黑質區(substantia nigra)——少數能產生多巴胺的腦區之一。
其中一位患者是一名年輕、富裕的紐約名媛,後以化名「Rose R」著稱。1926年,她入睡後做了一個噩夢——被困在一座牢不可破的城堡中。這場噩夢持續了43年,從未間斷。
1969 年,紐約年輕神經科醫生奧利佛·薩克斯(Oliver Sacks)被指派負責布朗克斯聖嘉民醫院(Mt Carmel Hospital, Bronx)約80名嗜睡性腦炎患者,包括「羅絲· R」(Rose R)。他注意到,他們的一些症狀酷似另一種疾病——帕金森症(Parkinson's)——的極端版本,因而決定以當時一種新興療法L-DOPA進行嘗試。治療開始後短短幾天,包括羅絲在內的患者醒來了,站起來、四處走動,並與目瞪口呆的醫護人員交談。
讓薩克斯震驚的是,這次甦醒非常短暫。對羅絲來說,大約只維持了一個月。部分患者維持得久一些,但最終全都不可避免地惡化。直到1979年,即十年後,羅絲被一塊食物噎住,她的噩夢才結束。
薩克斯用來讓「羅絲· R」暫時「復活」的藥物L-DOPA,是多巴胺的前體(precursor)。雖然薩克斯當時並不了解其機制,但後來對嗜睡性腦炎的研究有助於推斷羅絲的情況。儘管她的黑質區幾乎完全死亡,但仍殘存少量神經元(neurons),能把L-DOPA轉化為真正的多巴胺。而她的大腦長年缺乏多巴胺,對最微弱的流入都極為敏感,因此才會以劇烈活動回應——那短暫的甦醒。然而,隨著大腦重新校準,那微弱的一點多巴胺最終仍不足以維持正常生命。
基本上,嗜睡性腦炎展示了當大腦耗盡多巴胺時會發生甚麼:它停止運轉。移除多巴胺並不會讓大腦癱瘓,而是把它推進黑房間——進入無行動、無經驗的狀態,不再感到必須做任何事。除了基本反射,例如食物放入口中會咀嚼之外,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受多巴胺驅動。沒有多巴胺,我們人人都會被困在黑房間。相反地,如今我們醒著的每一刻都急著去做點甚麼,全靠多巴胺。
如此看來,我們每天與自己糾纏、總想做不該做的事,似乎全是多巴胺的錯。如果它負責激勵我們,為甚麼做得如此糟糕?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看看多巴胺真正在做的是甚麼。
不是「快樂化學物」
理解多巴胺最基本的方式,是將它視為「快樂化學物」。這種說法作為入門很有用,但其實是錯誤的。
問題在於,多巴胺並不會真正引起快感。如果你有朋友服用阿德拉(Adderall,治療多動症ADHD的藥物,透過擠出神經元內現有的多巴胺來產生作用),他們或許會說自己變得更專注、更有生產力、「進入狀態」,但並不會感到欣快。針對老鼠的研究也顯示相同結果:根據表情與爪部動作判斷,注射苯丙胺(amphetamine,安非他命,阿德拉同類藥物)會讓牠們更努力追求獎賞,但不會提升牠們的享受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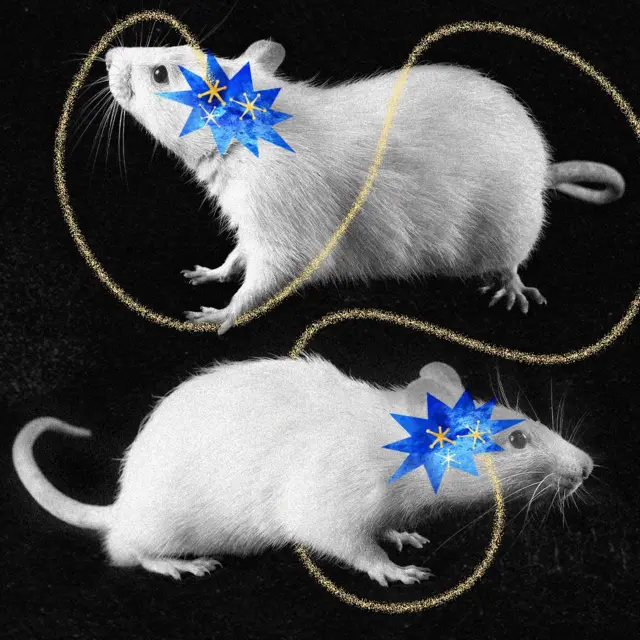
圖像來源,Serenity Strull
另一個較細緻的說法是,多巴胺是「再多做一點那個」的化學物。不是快樂,而是記憶。它幫助大腦記住哪些行為帶來成功。
只要有多巴胺釋放,那裏的記憶就更容易被強化,彷彿多巴胺在告訴大腦:「未來就多做剛剛那件事。」最清楚的例子是技能形成,發生在大腦的基底核(basal ganglia)。當一個人學跳舞時,多巴胺會挑選「成功的舞步」並保存下來,讓它們成為一組組合,可以一次性啟動,而不用皮層逐步思考。熟練舞者只需藉由情境——歌曲某一段落——觸發這段動作序列,它便會「自動展開」。我們稱之為「肌肉記憶」,其實是基底核的記憶,由多巴胺逐步優化動作組合而成。
這種「再多做一點那個」的邏輯,也延伸至其他接收多巴胺的大腦區域,包括皮層。多巴胺在成功後釋放,強化那些導向成功的神經元及其連結,我們會一次又一次回到這些神經路徑。
在皮層中,這可能不只是回到執行動作的神經元,也包括「思考該動作」的神經元。如果某個洞察突然讓你看清某個問題,你會獲得一陣多巴胺衝擊,而參與該洞察的神經元會強化。下一次,靈光乍現會來得更容易。如果某句歌詞觸動你,你也會獲得一陣多巴胺,而隔天起床,你可能腦中就盤旋著那句旋律。
照這個說法,多巴胺幫助我們選擇能達成目標的最佳行為與想法——成功時它告訴大腦「再多做一點那個」。
但這裏有個轉折:成功並不總會引發多巴胺。真正會引發多巴胺的是「意料之外的成功」。
這種解釋比單純的「快樂化學物」或「再多做一點那個」都更精細,但也把我們帶回黑房間問題。
誰決定甚麼是「預期」?誰比較出「現在發生的事」是比預期好還是糟?答案是:大腦皮層。沒有其他腦區有足夠資訊能理解,例如「金錢」——而金錢在人的大腦裏是可靠的多巴胺來源。因此,是皮層告訴獎賞系統何謂「意外成功」,並換得多巴胺。
但皮層的目標不是使現實與期待一致、並在一致時感到滿意嗎?那麼,皮層為何會主動刺激自己索取多巴胺?黑房間問題再度浮現。一旦我們否認多巴胺本質上能帶來愉悅,就難以理解我們為何會被推向那些能產生多巴胺的事物,或者說,我們為何會被推向任何事物。
「把這弄明白」
這仍是研究中的領域,而在我看來,皮層與多巴胺之間的精確關係,是整個神經科學中最未解的重大問題之一。
以下是我的理解——雖然將來我可能會被證明是錯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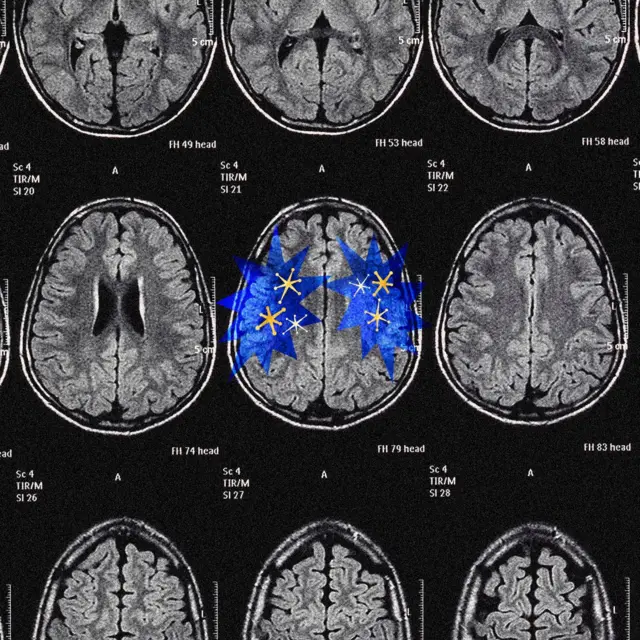
圖像來源,Serenity Strull
事實上,皮層想要的是「最少的多巴胺」,就像它追求所有活動的最小化一樣。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只要皮層辨識到某個情況「比預期更好」,它就會獲得多巴胺——事情的連線方式就是如此。
與其把多巴胺視為正面、愉悅的訊號,我認為更合理的是把它視為一種「命令」訊號:把這弄明白。對皮層而言,「弄明白」就是讓現實與期待一致,而這可以透過改變現實或改變期待來達成。我猜測,多巴胺可能會把天秤推向「改變現實」那邊,迫使我們行動,而不是接受現狀。不過,截至目前,我並不知道有研究能確定證明這一點。
如果把多巴胺視為「把這弄明白」的化學物,就能解釋苯丙胺對人類的影響,以及多巴胺缺乏對動物的影響。這解釋了為甚麼阿德拉會讓人產生「隧道視野」。也解釋了為甚麼多巴胺水平低的人會缺乏動力。
這同時也解釋了我們對不確定性的迷戀。
這並非人類獨有。相關研究最初在鴿子身上進行,後來也在其他動物身上被重複驗證。你給鴿子一個按鈕,按一下就有獎賞。然後你開始改變每次獎賞需按下的次數。按得越多——例如50下或100下——牠們完成後越疲憊,也越不願意繼續按。
但若你讓這個數字變得不可預測,鴿子就不會停。牠們會不斷按、反覆按,不管獎賞出現多少次。激勵牠們的並不是獎賞本身,而是尚未破解的模式。
更有趣的是,假設你再度把鴿子放進籠子並設一個按鈕,但這次獎賞完全隨機發放,與按不按無關。沒多久,有幾隻鴿子開始按按鈕。最後,全部鴿子都會按。牠們全都陷入試圖破解不存在的規律中——於是憑空捏造規律,逐漸相信是自己創造了獎賞。
這一切聽起來是不是相當熟悉?這正是賭博與社交媒體令人上癮的原因:不只是金錢或社交回饋,而是回饋的「不可預測性」。你永遠不知道Instagram上哪張照片會獲得大量按讚,也不知道哪支TikTok影片會突然爆紅。賭場和社群媒體平台透過隨機發放獎勵來放大這種不可預測性——他們當然很清楚這些針對鴿子的實驗結果。試想,如果你的所有「按讚」都在每週一次、固定時間集中送達,你大概會開始害怕那一天——因為多半不會比預期更好,反而大多比預期更糟。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似乎永遠與自身動機失調,原因也就清晰了。多巴胺並不會把世界標記為「好」或「壞」。若真如此,我們只要做「好事」、避開「壞事」,永遠保持動力就好了。相反地,多巴胺標記的是「意外的成功」——無論我們如何定義——並告訴我們:「把這弄明白,讓成功變成常態,不再令人驚訝。」
聽起來也許有點沮喪。如果多巴胺真是在向大腦傳達這種訊息,那無論我們做甚麼,最終總會感到厭倦與不滿,而這正是重點。但換個角度來看更好。對無聊的恐懼、對不滿的陰影,正是我們做新事物的理由。新事物能帶來意外的驚喜——那些罕見、難以預測的小小喜悅,讓生命值得一活。
從演化角度看,這套系統也極為精妙。想像兩隻動物,一隻對現狀完全滿足,另一隻容易厭倦,永遠尋找更多。哪一隻比較可能長期生存?多巴胺是在押注未來的必然變化。演化偏好那些坐立不安、不滿足、追求新奇、被「更多」幻象折磨的個體,因為這讓他們不會停下腳步,最終更有生存優勢。
至於內心平靜——嗯,那本來就不是必需的。
本文節選自腦神經學家尼古拉·庫庫什金的著作《單手拍掌》(One Hand Clapping),英文版初版於 2025 年 10 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