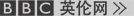文化鴻溝:拽下你的蓋頭來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面紗、蓋頭都劃歸色彩繽紛的民族服裝,與維吾爾人歡快的音樂和舞蹈聯繫在一起。
電影裏看到帶著面紗蓋頭的邊疆婦女,同當時身邊那些樸素認真的北京女性比起來顯得豪放自在,她們的生活充滿了情趣和感染力。
蓋頭作為一種魅人的服飾,通過那首頗為流行的歌曲也滲透到我的潛意識中:
掀起了你的蓋頭來 讓我來看看你的眉
你的眉毛細又長呀 好像那樹梢的彎月亮……
從彎月般的眉毛唱到秋波似的眼睛,再唱到臉蛋,唱到嘴唇,讓人感到蓋頭下的女人神秘美妙,但沒有覺得她受到什麼委屈壓迫。
形像逆轉
後來,蓋頭在我心目中的形相卻出現了逆轉。
什麼時候開始我已經不記得,但我學得它是伊斯蘭傳統社會男人壓制女人的符號,同中國歷史上給女人裹小腳,歐洲歷史上讓女人穿束胸一樣,是殘酷、愚昧和束縛的象徵。
在我70、80年代上學和開始工作的倫敦,蓋頭(往往是黑色的)主要限於電視屏幕上看到的阿富汗或伊朗,報道中間時時穿插著婦女傾訴被迫穿戴這種服飾造成的壓抑和屈辱。
至於在英國本土,雖然過去幾十年有不少中東和南亞穆斯林國家的移民遷來,但直到20世紀末年,蓋頭也只是非常偶爾才看到。
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子和親屬當中來自穆斯林國家的人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著此裝束。
自己的選擇
然而,「迄今為止」在這裏恐怕是個關鍵詞。
過去十年,英國街頭戴著蓋頭的穆斯林婦女明顯增多,很多都是年輕人,在我住的街上天天都會看到。若有哪個親戚或朋友的孩子突然戴上,我現在可能也不會太驚訝。
在當代英國,這通常都是個人的選擇,而並非屈從於家裏或外邊的壓力。可是一個人何以要做這種選擇?她身邊的人看到了,又會作何反應?
這正是現在倫敦舞台上一齣話劇探索的主題。
法蒂瑪做了什麼
在漢普斯特德劇場(Hampstead Theatre)上演的《法蒂瑪做了什麼》(What Fatima Did)展現的是一群活潑放蕩、不拘小節,總體而言也還算挺有腦筋的倫敦高中學生。
這個朋友圈子包括黑人、白人和穆斯林家庭的孩子,大家無拘無束,宗教和種族在他們之間好像根本都不看在眼裏。
但他們其中一人,就是劇名裏的法蒂瑪在她18歲生日的前夕突然一反常態,停止吸煙喝酒耍斗,也斷絕了同白人男朋友喬治的來往。
耍把戲
劇作家玩的一個小把戲是讓法蒂瑪這個主人公從頭到尾都不出現在台上,而完全憑著她幾位同學的議論帶出她的人品性格和理念,同時也展現他們自己。
年僅21歲的劇作家阿蒂亞·森·古普塔(Atiha Sen Gupta)不僅寫出了一個接一個緊湊的,充滿活力的場面,而且人物縱使有代表性,也還是活生生的,有個性的人物,絕非死板的典型。
昔日男友喬治想知道法蒂瑪何以產生如此怪念,屢遭冷遇後終於找到她時因為一時激憤拽掉了她的蓋頭。他為此落下了一個施展種族暴力的罪名,面臨被學校開除的懲罰。
在朋友圈子裏一直維護孿生妹妹自決權的莫哈默德雖然和喬治大打出手,自己也蒙在鼓裏。他搞不清妹妹(還是姐姐?)的動機,只是絕不容許別人對她輕蔑。這甚至也包括他們的母親。
寧願要女兒是個一條腿,懷了孕的妓女
這對雙胞胎的母親對女兒的決定憤怒之極,說她寧願女兒是個只有一條腿,懷了孕的妓女,也不要她戴蓋頭。
「我為了自決權而和你爸爸分手,我和你姥姥,再往上還有你的曾姥姥都為了擺脫夫權的束縛而拼斗,這蓋頭是血染的,怎能自己戴到頭上!」
然而,女兒生活在另一個世界裏。她看來並未把蓋頭視作父權/夫權壓迫的象徵,而在多元文化的21世紀英國,覺得戴上蓋頭展現的是她對自己文化的自豪,和對種族主義者辱罵的蔑視。
話劇最終既沒有讓法蒂瑪現身舞台,也沒有表白作者對蓋頭的理解究竟傾向哪邊,但為觀眾提供了樂趣和思考的空間。
首創的話劇能如此生動地、多層面地表現這場理念的搏鬥,作者未來想必定還有好戲給我們看。
(鴻岡 2009年11月01日)
讀者反饋
我是自願戴頭巾(蓋頭)近20年的穆斯林,戴頭巾表示服從造物主的指示,和壓抑和屈辱沒關係。請看我寫的文章:頭巾不容易 http://tw.myblog.yahoo.com/oyaos/article?mid=70 謝謝。
oyaos,
鴻岡的文章看似閒聊,總是給讀者帶來思考。
其實我同意很多事情不太容易隨便去判斷對錯,只要不涉及危害別人的利益,當然在特定環境裏,取得別人的信任,讓大家都有安全感又很重要,如果戴頭巾的話, 有時候很難得到其他的信息,比如喜怒哀樂等表情,好像有人統計過,人類交流溝通,實際上文字信息只佔50-60%,表情,肢體語言,語氣等也可以傳遞很多 信息,如果帶了頭巾就難理解這些信息了
鴻岡的粉絲, 愛丁堡
雖然我是一名男性,但是我卻十分同情受夫權父權壓迫的女人,在中國廣場上的和平鴿會被人吃掉,在日本家家門口養的紅金魚沒人去撈,但在中國也會被撈著吃了,在這種情況下,內心是不會有一刻平靜的,根本也不想享受壓迫別人帶來的快樂.
Baish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