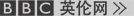文化鴻溝:是什麼人喝什麼酒
很多英國人喜歡喝酒,同時又喜歡批評別人的飲酒習慣。我擔心自己也在這個行列之中。
自己喝,那當然都是健康適量,享受人生,但輪到別人,不是自我摧殘就是危害他人,擾亂治安。
前幾天,西英格蘭大學(UWE)剛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說,在英國因為飲酒過量造成的死亡從1984到2008年間增長了將近兩倍,從3054人增長到8999人,而且預告未來十年數字顯示繼續上升的趨勢,所以問題並非空談。
國際排列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統計,英國人的酒量在世界將近200個國家中排行18。老大是烏干達,老二是盧森堡,再往下是捷克、愛爾蘭和摩爾多瓦。
不過老大的頭上有個問號:無論烏干達還是其他幾個飲酒較多的非洲國家數字都不太精確,因為當地很多人飲酒是私下用高粱或小米釀製的啤酒,雖然WHO參照的是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數據,但還是承認這裏可能有水分。
幾個歐洲國家的數字應該比較準。在2003年,這些國家15歲以上人口一年裏人均喝下去的酒按照純酒精含量來算,盧森堡是17.5公升,捷克是16.2公升,愛爾蘭14.5公升,摩爾多瓦13.9公升。
與這樣的數字相比,英國人的10.4公升顯得還算收斂,儘管這比中國人的4.5公升高出一倍多。
歷史根源
無論在什麼地方,不同人群的飲酒都有差異,年齡、性別、民族、階層、地域都有會影響。
英國政界眼下尤其矚目的是青少年的酗酒:有人覺得這個問題的出現表明法規太松,或是政府對造酒業渲染的管制缺乏力度,乃至認為這是社會的墮落。如今,政府和反對黨也都努力證明自己最有決心和能力應對這個問題。
然而這些聽著都有點舊調重彈的感覺,因為酗酒之邪惡,酗酒對社會的摧殘,在英國曆來都能聽到各種危言聳聽的告誡。
起伏
現在,曼徹斯特大學出版社出的一本新書《酒的政治:英格蘭飲酒問題的歷史》(The Politics of Alcohol: A History of the Drink Question in England)對這些探根索源,發現至少從16世紀中期開始,就時不時有人出來呼喚。
書的作者詹姆斯·尼科爾斯(James Nicholls)說,英格蘭人的飲酒量過去幾百年一直時有起伏,其中19世紀後葉的飲酒量尤為高漲。
相比之下,20世紀的頭半個世紀,英格蘭人飲酒遠遠低於歐洲許多國家,直到1960年代初才開始增長。不過現在確實是飲量較高的時期,所以引起關注不無道理。
不過為什麼大家的注意力通常對準某些人群,而非整個社會?
階級差異
尼科爾斯說,以17世紀初年為例,那時候議會制定通過了一系列管制啤酒屋(ale houses)的立法,因為這些通常是社會底層的人聚集的場所。
相比之下,中產階級去的高雅一點的酒店(taverns)則沒有太多管制。
當時說出來的雖然是整治遊手好閒、滋事鬧事和醉酒問題,但是有一派理論認為,對那些百姓聚會的場所加強管理,實際上是要施展社會控制,因為當政者擔心到這種地方喝上幾杯之後,有的人就該以為自己的論點興許比議會裏的更高明瞭。
喝葡萄酒提高素質?
除了場所的區分之外,英國不同階層喝不同的酒,也是歷史傳統,一直延續至今。
當初的啤酒屋顧名思義是賣啤酒,而tavern裏面喝的則主要是葡萄酒。17世紀英格蘭內戰年間,保皇派也是喝葡萄酒,借此展示自己的貴族氣派以及和歐洲大陸文化的聯係。
尼科爾斯說,君主制復辟後,啤酒和葡萄酒便日趨成為區分社會不同階層和政治立場的符號,高貴者喝葡萄酒,庶民百姓喝啤酒。
到了17世紀末年 ,從荷蘭引進的烈性酒琴酒又逐漸在英國流行開來。由於早年管理得比葡萄酒和啤酒松,很快流行開來,以至後來被看作許多社會弊病的源泉,從18世紀中期便立法嚴加管制。
葡萄酒的地位卻仍然高尚。到1860年,後來曾四任英國首相的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還推動立法,讓貧民區的飲食店賣葡萄酒,以圖提高這些地方的國民素質。
理性抉擇
現在英國政府對如何限制飲酒的考慮較多的一個是增稅以抬高售價,一個是健康宣傳,讓人提高警覺。
參照歷史,尼科爾斯覺得這能有多大效益?他說價格似乎確實有作用,不過利用市場機制,指望的是人們作出理性抉擇。
然而事關喝酒,理智到底能對人的行為有多大支配力,難免存在疑問。
(鴻岡 2009年10月22日)
讀者反饋
我認為飲酒有些逐步【坦誠相見】的意味,大家一旦喝過酒,至少是微醺以上,就有些增進感情的元素了,不過這種增進感情的方式比較適合男性。
lulu, China
最要緊的是喝醉了以後幹什麼,若是像李白那樣吟詩唱誦,還是滿有趣的,喝啤酒的就來一通「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騰入海不複回」,喝葡萄酒的就「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英國的酒館若是造就出些詩人來,也不枉為莎士比亞的故鄉
未署名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