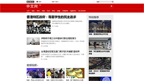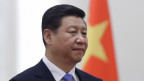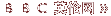陳光誠今年5月抵達美國紐約
中國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今年4月從山東逃離軟禁,現在美國學習。BBC視障人節目「接觸」(In Touch)近期前往美國紐約製作陳光誠專題節目,節目製作人郝曦同時為BBC中文網專訪了陳光誠,談他在美國的近況及他對中國法制的思考。下面是專訪的文字內容:
記者:來美國後現在你的家人和孩子在這裏是否已經安定下來?你們的日常生活適應了嗎?
陳光誠:我覺得現在是比較安定了。孩子們上學了。我們倆也在上學。其他的時間也在做我們想做的工作,在這個研究所裏開展有關憲政的研究。我覺得基本上都安定了。但有一點,這七年來被他們折騰的身體確實受到了很大的傷害。雖然自己覺得已經恢復得差不多了,但真正投入到工作當中的時候還是有非常多的反應。比如說,我以前暈車的程度完全沒有那麼嚴重,現在有時坐十幾分鐘的車就會有非常明顯的暈車感覺。因此我覺得對我身體的損害還需要一段更長的時間來恢復。
記者:哪些方面感到有困難或遇到了障礙?
陳光誠:我覺得最大的障礙可能就是語言交流的障礙吧。這個困難我需要盡快克服它。我現在從周一到周五幾乎每天都有英文課。我覺得,通過慢慢的學習掌握語言才能克服這個困難。
記者:除了學英語,我們知道你最關注的是學習法律。現在在法律學習方面是如何進行的?
陳光誠:我的法律課已經開始。我是從學習美國的《獨立宣言》開始的。現在在學習美國憲政當中的憲法和修正案。
記者:學習美國法律對你以後在中國的工作或者今後做同中國相關的工作會有幫助嗎,有用嗎?
陳光誠:肯定有幫助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幫助。 中國有句話叫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想公平正義、人類的善良都是沒有國界的。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尊重人權、博愛這些都是普世的價值,不存在國界的問題。在學習美國法律的過程中我發現很多問題,這些問題將來可能在中國避免發生。我想這是為中國的將來做準備的。我覺得是非常有用的。
記者:雖然你學習的時間還不長,但到目前為止,你學習過程中所接觸到的美國的法律、美國的憲法中,哪些東西給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陳光誠:最深的印象就是美國的修正案當中關於限制立法權的一個內容。這是中國法律所沒有的。這個修正案非常明確的指出,美國國會不得立法限制公民權利。我認為這個理念是極為重要的。這是我印象最深的。這也是美國的憲政和修正案同中國憲法不一樣的最大區別。
記者:聽說你也想學國際法?
陳光誠:對。
記者:你是希望在國際舞台上也能發揮一定的作用?
陳光誠:不僅僅是這個問題。我究竟能起多少作用,這要順其自然。最重要的是,現在很多國家,包括中國都有這樣一種說法,就是說「這是內政,反對別人干涉」。我認為是不是內政需要有一個限度,一個標準,而並不是說你說內政就是內政。這就同一個家庭一樣。兩口子之間普普通通的拌嘴,或其他一些行為,這都可以接受。但任何一方,無論男方還是女方,都沒有權力將你的愛人殺掉或打殘,沒有權力去虐待她(他)。如果超出這個界限的話,這就不是你的家事了。就需要家庭以外的法律來對你做出約束。那麼國家之間也同樣是這樣。如果你是在國內堂堂正正的做事情,堂堂正正的執法,當然其他的國家是不能干涉的。但是如果你自己就違反自己的法律,關起門來去虐待自己的公民的話,那麼我認為國際法應該有這樣的約束力,無論對哪個國家。即使現在不起到這樣的作用或還沒有起到這樣的作用,我想國際法的發展趨勢也應該在將來對所有國家都有這種約束力。
記者:我們知道,使你遭受七年關押的主要原因可能還是同計劃生育和地方政府實施計劃生育中的暴力行為,強制墮胎有關。那麼在這一方面,據你了解目前是否有任何改進,任何變化?
陳光誠:我覺得還是有一些變化。以前單純是靠暴力來維持計生,維持人口標準。像強制墮胎,強制結扎幾乎都曾是唯一的方法。但自從我們關注這個事情之後,現在他們雖然沒有完全停止下來,但事實上還是有所收斂。至少說對於那些已經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人現在是採取按照計劃生育法「征收社會撫養金」的形式進行。當然,社會撫養金該不該收,這是另一個問題。但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收斂。
記者:你是否曾考慮過當時你所做的事情代價太高了,特別是對你的家人來說付出的代價太大。有沒有想過也許應該停下來?
陳光誠:當時應該是考慮到了的。因為在那種情況下,什麼都可能發生。我很清楚這一點。但是我無法忍受那種父母被強行拖走,孩子在家裏那種撕心裂肺的哭聲。那種處境讓我聽到那種聲音,我真的無法考慮到自己的安全而保持沉默,我做不到。
記者:那麼你那時也一定同妻子袁偉靜談過,你們兩個人都很清楚會有什麼危險。你們是否一致同意你應該堅持做下去?
陳光誠:是的,我妻子也很支持我。我想任何一個善良的人看到這種情況都不會袖手旁觀。
記者:她(袁偉靜)是否曾經跟你說「光誠,夠了,不要再作了」?
陳光誠:沒有,她從來沒有跟我這樣說過。
記者:其他人有沒有表示過關心,或提醒你要非常謹慎?
陳光誠:這方面的提醒非常多。直接的威脅也非常多。
記者:這種威脅是直接對你,對你家人的威脅?
陳光誠:都有。
記者:你在監獄裏度過了四年多的時間。而後又被非法拘禁了近兩年。在這期間你和家人遭受了許多折磨。那麼是什麼信念使你堅持了下來?
陳光誠:我覺得人類的善良是不可能用暴力來摧垮的。
記者:你遭受過很多這樣的暴力嗎?
陳光誠:當然。
記者:你認為這在你一生中會給你留下什麼影響,什麼痕跡?
陳光誠:讓我努力去改變這種不人道的、非人性的、非法的、突破了人類道德底線的這種環境。非做不可。
記者:在這種情況下你最後決定要逃出來。為什麼作出這個決定?
陳光誠:為什麼要作出這個決定?我要爭取我的權利。
記者:你從臨沂逃出,到達安全地方的第一件事是向溫家寶總理髮出呼籲,提出三個要求。你為什麼當時選擇向溫家寶總理提出這些要求和申訴?你是否覺得他比其他中國領導更有「親民」的口碑?
陳光誠:我覺得是。當然,我不管向誰提出來可能都會有人問這樣的問題。我向溫家寶提出來你會這樣問。我如果向胡錦濤提出來那你可能又會問為什麼不向溫家寶提。但我的看法是,不管向誰提出這樣的問題和要求,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衡量標準,就是不管他們平時說什麼,最重要的還是要看他們做什麼。說得再好,不做也沒有用。這一點我當時在視頻裏也說得很清楚。我們將拭目以待,他們如果調查,那說明一個問題。他們如果拒絕調查那說明另一個問題。所以我覺得最重要還是要看他們的行動。
記者:我之所以向你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我想很多聽眾都非常關心你今後會扮演一種什麼角色。你希望今後自己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呢?
陳光誠:我想我能扮演什麼角色我真的沒有辦法回答。但是我相信我在推動社會的公平正義,推動中國公民社會的建立,推動人權、民主、法治、憲政等這些普世價值上我會盡我的全力。
記者:你覺得作為一個殘障人,如果今後想改善中國殘障人的生活,改善殘障人的權益以及各方面的情況,你認為通過什麼途徑可以起到最好的作用?
陳光誠: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一個工作是給殘疾人機會。居住在中國農村的殘疾人實際上是沒有任何的機會,甚至連走出家門的機會都沒有。所以說,我們今後開展對殘疾人權益的保護就應該給殘疾人提供信息,讓他們了解很多事情。然後向他們提供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意願的這樣的機會,然後再創造一些讓他們參與的機會。當他們具有了這些機會以後,我認為他們會想盡辦法去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殘疾人自己懂得維護自己的權利。這才是最重要的。靠別人給予的權利是長久不了的。所以只有殘疾人本身明白了「我的權利只有靠我自己去不斷爭取和維護才能長久」這個道理,只有明白了這個社會如果不公正 的話我們的權利也沒有辦法維護,因此在維護自己權利的同時考慮到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做到這兩點以後殘疾人的權利肯定能得到維護。
這裏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我們每個人生活在這個社會上,對這個社會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只有我們每一個人都對這個社會負責任的時候這個社會才能變得更好。現在坐下來談的時候很多人都在埋怨這個社會如何的不公正,如何不好。但是很少想想自己為這個社會變得更好,變得更公正都作了些什麼。哪怕你在關鍵的時候說一句公道話,或者說投去一個正義的眼光,你在發現別人做惡的時候投去一個憎惡的眼光,讓他感覺出來你知道他所做的惡行,這一切對於一個社會的良性循環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對這些善惡都沒有任何明確表示的話,我想這個社會的善惡真的可能就不重要了。如果對所有的善惡都有非常清晰的認識,而且從行為上表示出來對於惡我們要讓他沒有生存的空間,對於善我們要大加讚賞的話,這個社會將會變得更好。這一點我覺得對於每一個最普通的公民來說都是最重要的。而且不僅僅是想想,說說,如果能付諸行動,哪怕是小的行動的話這個社會會變得更好。
記者:也就是說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
陳光誠:對。我認為中國的公民對自己負責任,這是中國公民社會建立的一個基本前提。我們看到的可喜狀況是,中國的公民社會成長得非常迅速。
記者:據你了解的情況,中國殘障人現在的法律意識,他們的維權意識是否比原來增強了?
陳光誠:我覺得是比原來強。當然這也取決於信息的流暢程度。還有別人在某種程度上的啟發。這都非常重要。
記者:最後我想問一下,你希望什麼時候回到中國?
陳光誠:這個我想我無法回答你。我只能說,在合適的時候吧。